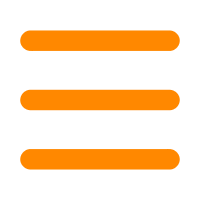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近期在《念书》上成为一个话题,自6月号以来陆续有 文章发表。伦理学是古之显学,经济学则是今天的显学,有时甚至被批评为“经济 学帝国主义”,察看两者在今天的关系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况且这一问题还涉 及到大家今天社会很多问题的解决之道或讲解之道。所以,我目前也想借这个话题 谈一点阅读亚当·斯密著作的领会。
斯密一生的主要著作就是两部:一部是《道德情操论》;另 一部就是奠定了近代经济学学科基础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缘由的研究》。斯密被视作是经济学的开创者,他同时又是一个 要紧的伦理学家。一些经济学家引斯密为典范,觉得经济学家也应关心道德问题, 也有的经济学家则觉得斯密只不过个例外。
斯密的著作读来亲切有味。斯密第一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察看者,伯克在对《道德情 操论》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书中的例证丰富而且确切,表述平易而生动,表明作 者是一个具备非凡察看力的人,能使事物完美地呈目前大家面前。这一评论不只适 合于《道德情操论》,也适用于《国富论》,只不过前者主要察看大家内在的情感活 动,而后者则主如果察看大家的外在经济行为。斯密与康德一样终身未婚,一生也 大半在学院里和书斋中度过,但从其书中却可看出其知人甚深——知普通的人性和 人心甚深,这种常识构成了他展开理论讲解的一个制约性基础。
斯密早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过英国文学的课程,还喜好过诗,不过,他具备无 须等待社会上作出判断就领悟自己失败的分辨能力。他非常快就发现他的天职是在学术,在一七 五○——一七五一年,他讲授过一个冬季的经济学,这份经济学讲义中已经有了自 由贸易的思想。不久他又获选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随后转任道德哲学 教授。根据苏格兰大学当时的学科分类,逻辑学包含修辞学和文学,道德哲学则包 括四个部分:神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由此大家可以想见 当时“道德哲学”学科的广博性,与对教授所需要的常识的广博性。可惜这全部 “道德哲学”的讲义原稿都在斯密的坚持下,让他的朋友在他去世前烧毁了。后来 出版的《有关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只不过一个学生听他讲3、四部分 的课堂笔记。当然,《道德情操论》事实上就是从他第二部分的讲义中进步出来的, 而在第四部分讲义中,也包括了后来《国富论》的基本胚胎。
这四部分的具体内容如何,它们之间是怎么样联系的,它们是不是构成一个体系? 据斯密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米勒说,斯密在第一部分中考察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和特质, 与作为宗教基础的人类大脑活动所需要遵行的各项原则。其时社会还没那种“ 上帝去世了”的震惊和挑战,神学的地位和内容主要还是沿袭,这方面看来并非斯 密注意的重点所在。第二部分大家从《道德情操论》可以看出,这部分内容是一种 较严格、狭义的伦理学,而特别是一种涉及个人的道德心理学或心态学,但它仍然 主如果围绕着行为的适合与合宜性,围绕着正义与德性展开的,而并不是全方位地论述 人的精神世界或心灵最高境界。第三部分即法学部分,据米勒说,斯密在这部分详 尽地论述了与正义有关的那部分道德学,亦可说是一种涉及政治规范的伦理学,而 其中也包括了法律社会学和法律史的内容,斯密遵循了孟德斯鸠的办法,在公法与 私法两方面,追溯了从野蛮时期一直到文明年代的法学演进,与怎么样相应地引起 法律和政府的改变的演变。而在第四部分即政治学部分,斯密考察了那些不是打造 在正义的原则上,而是以权宜原则为基础的行政法令。并考察了那些以促进国家的 富强和兴盛为目的的行政法令,探讨了与商业、财政、宗教和军事建制有关的各种 政治规范。
大家或许可以如此说:3、四部分的内容构成了伦理学的主体,这一伦理学 包含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两个方面,只不过 前者尚偏重于个人伦理学的一个方面,而后者有的内容如法律社会学的内容是在伦 理学的范围以外。这也基本上符合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其次是德性的形而上学原理。康德的体系形而上学色彩远 为浓厚,从内容到办法都更看重理性,看重逻辑的推演,这与看重情感、经验和观 察的斯密相当不同。相同的是,他们的学术都有努力脱离神学而独立的倾向,不过 康德主如果为理性争地位,斯密是为经验和情感争地位。看重哲学思辨的康德伦理学是从一种形而上学的 基础推出,而看重经验察看的斯密伦理学则向经济学延伸或者说“扩张”,前者较 缺少经济学的内容,后者则没明确的形上学的基础。
斯密也确曾想过要系统地讲解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与它们在历史上的变 革,其中不只涉及正义,也涉及其他任何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他说他的《国富论》 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岁收和军备问题上是如此。他在一 些著作和信件中,也曾把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合称之为“我的体系”。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古典的、包括四个方面的“道德哲学”体系是让人神往的 一种体系,它既有向上和纵深的维度,又有向法律政治、经济等社会规范的横的延 伸。经济学在当时还没独立的学科地位,它是包括在第四部分“政治学”的范畴 之内的,而“政治学”又放在“道德哲学”的名下。所以,今天大家在《关于法律、 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读到后来进步为《国富论》的一些思想是放在“论警 察”的一篇中是会感到有的奇怪的,但当时的学科分类状况就是这样。斯密自己比 起看重《国富论》来好像也更看重我们的《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不止是 他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也是他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全力以赴进行修订的一本 书,他在身患重病、了解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的状况下,对这本书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一 次修订,这说明了伦理学在斯密心目中的地位。对于道德真理的探讨在斯密那里是 贯穿一直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生平与著作》的作者斯图尔特所说:“这类崇高 的真理在他年轻时离开学院之际,首次激起了他的天才的热情,他最后的精神努 力也是寄托在这方面的。”
但在迄今为止的后人看来,显然一般都觉得《国富论》要比《道德情操论》更 为要紧,在斯密的墓碑上写的也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安眠于此”,斯 密被视作是现代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和开创人,而他对现代伦理学的影响 却不如康德。康德使伦理学立足理性,并摆脱目的、成效方面的争议,打造了一种 以规范为中心的常见主义的伦理学,这显然更符合近代向价值多元社会进步的趋势。 康德的伦理学可以在原则规范方面交流社会范围与个人范围,斯密的伦理学则较集 中于个人的道德实践和自我控制,特别是对大家道德情感的剖析,其剖析独到、深 刻。但这方面内容固然要紧,在今天的社会里却毕竟落入了第二义,对何为正当, 何为合宜的问题在纷争的现代社会无疑需要更优先地予以说明和论证。不过,将来 年代会不会变化得使斯密的道德理论更为要紧亦未可知,如若其然,那肯定是一个 比目前更为幸福的年代。
斯密的《国富论》之所以较之《道德情操论》发生了更大影响,还与经济生活 在社会中愈加占据中心地方,经济学也愈加进步有关。近代以来很多新学科的 打造,总是历程了一个第一摆脱神学,然后又从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中离别出来的 过程。而斯密也确实适应了年代所需,在理论上对当时已经呼之欲出的很多经济学 思想做了一种相当完美的综合,这不只要归因于他的天才,也要归因于他所投入的 劳动量,归因于他的严谨、细致和长期不懈的努力。
《国富论》是相当独立的一部经济学著作,斯密并没让他在《道德情操论》 中表达的道德看法进入该书起支配用途,这后一本书并非以前一本书进步和推演 出来的,它们确实有着相当不一样的主题、范围和重点,有着不一样的剖析办法。斯密 在前书中强调同情、强调利他和自制,但他并没试图在后书中以此来规范大家 的经济行为。后书中所表现的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独立的经济剖析。当然最后的 目的还是明显的,即指向“国民财富”、“国富民裕”,斯密把这视作是政治经济 学的目的,但他觉得这一目的并不是能通过个人的禁欲和利他加上严格的政治控制来 达到,相反,它倒是可以通过个人分散、自由的自利行为来达到。
斯密两书看起来的分立事实上正表现了人的两面性,即一方面人是更关心自己 的,自爱自利的;其次人也有一种同情其他人,从而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检讨和自 我节制的能力,这种同情和自制是通过设身处地、对自己心灵中的“一个理想的旁 观者”发生共鸣,从这个第三者的看法进行察看来达成的。罗尔斯正义论的“原初 状况”设计过去从这一看法中得到启发。人类有两面性,然而这人类还是同一个人 类,所以,斯密两书的陈述又可以说是一致的,都是从不一样的侧面来讲明和讲解人 的活动。
两书的内容在一些要紧方面也是相互贯通或包容的。比如“看不见的手”的 著名比喻,它是提出来为自由贸易和自由经济的思想辩护的,而这一思想可说是斯 密经济学的主旨。在《道德情操论》中,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思想和比喻。更早,在一七五五年,斯密在一篇未发表的 论文中也陈述了反对政府干涉、倡导让事情自然进步的看法。在学生记录的《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 中也有同样的见解,这说明这一思想在斯密那里是始 终一贯的,并且不与他的道德看法冲突。
斯密为一种自由市场经济,或者说一种自由放纵的资本主义辩护,这一辩护是 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从行为和方法上,斯密赞成事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进步过程, 反对国家对个人的外在的、强制的干涉,由于,在斯密看来,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 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我们的行动原则,掌权者和计划者不可以像用手摆弄棋子一样来 随便摆弄每个人,计划者不可以把别人看作是借以达到 某种目的的工具。这就使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包含“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也具备了 一种道德涵义,而这一点总是不容易为人注意。另一个辩护则是从成效上辩护,即认 为叫人们自由地追求各自的利益,反而要比叫人人设立追求公益的目的更能促进社 会利益。因而,这一对成效的辩护同时也就是对大家的自利的行为动机的辩护了, 或至少是一种认同。因而,国家干涉个人经济活动在效率上和道德上都是不可取的。
但,虽然斯密觉得人的自爱本性是更为根本的,他并不认可孟德维尔的看法, 他不认可孟德维尔把自爱说成是自私自利,说成是恶,然后说正是恶导致了善,斯密宁愿把自爱看成是道德上中性的。他更不是倡导大家可以在经济活动中 任性妄为,或者说,无论大家如何追求自律都会促进公益。斯密事实上是提出了某 些限制和约束条件的,这类限制条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个人的约束, 即前述的鼓励大家的同情心和需要自制,这方面的内容主如果在《道德情操论》中 讲解的,在这方面的调节原因中,斯密强调三种德性:出于明智的小心;出于道德 的正义和超越于正义之上的仁慈,而特别是强调正义。其次的限制则是在规范 方面的,即确立一种完全的自由角逐的规范,斯密的建议似是说,自由的弊病看来 也只能通过自由来纠正。他相信通过自由角逐,排除所有专断的干涉,大家的自利 愿望就会变成有益于社会的力量,角逐的结果将迫使产品的价格降到与生产本钱一 致的自然水平。今天的大家自然都了解完全的角逐不可能,完全纯粹和理想的东西 都不会在日常存在,大家常常得寻求某种中道,但即使在混合的规范中,也还是 要承认有一种主导趋势,与到底应赞成哪一种主导趋势。在国家与市场之间更偏 重于哪一端,一直还是个问题。
大家的叙述事实上一直在斯密的两本书——在他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穿行。 综上所述,大家可以说,这两方面在斯密那里并不冲突,甚至不是截然分开的,斯 密的两本主要著作事实上也是交替创作,穿插修订的,而这两本书又都放在“道德 哲学”的更大范畴之下,而且他本人也更重视他的伦理学著作。从斯密整个治学的 初衷和归宿来看,说他第一和一直是个伦理学家倒也并不为过,甚至说经济学是由一个伦理学家创立的更不是完全不能——一个 新学科大概总得由并不是这一学科的专门家的人来创立。《不列颠百科全书》“斯密” 辞条的作者说《道德情操论》奠定了《国富论》的心理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续篇。 《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的作者科斯洛夫斯基也径直说,“政治经济学是产生于道德 哲学的”。
但,大家前面说过,《国富论》并非《道德情操论》的推演,而是客观的、 独立的经济剖析的结果。它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是说教的,而是剖析的,甚至《道德情 操论》也多半不是说教而是剖析描述的。并且,两书共执是同样的人性观,同样注 意到人的两面性,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两书也共执两样的道德观——一种作为公 正的道德。只不过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主如果从个人情感的角度察看,而在《 国富论》中,是从社会、规范的角度察看。这里重点的是怎么样理解“道德”的定义。 “作为公正的道德”与高尚的仁慈、自我牺牲不同,其要义是要在一些基本界限上 有所不为,用斯密的话来讲,对个人来讲甚至是如此:“大家常常可以通过静坐不 动和什么事都不干的办法来遵守有关正义的全部法则。”而对规范来讲也就是尊重自然 而然的演化过程,除非有某种更要紧、更迫切的道德考虑,不应付个人的经济活动 加以干涉和强制。这并非说要绝对地反对政府干涉经济,而是说干涉应比不干涉 提出更多的道德理由。
而大家今天的争论者双方有时可能都误解了如此的“道德”定义,于是就或者 通过完全拒斥道德来试图捍卫经济学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或者强烈地需要诉诸道德, 但却是一种需要规范与个人达到比公正更高的“道德”,或者是把“公正”理解为 一种“状况的平等”。《经济学家和说教者》的作者施蒂格勒并不倡导经济学家去 进行道德说教,但他却中肯地指出了市场交换的自愿性与重复性所隐涵的道德意义: 第一是它的非强制性,与它具备不同于政治和军事买卖常常损及一方的特征:它 一般是互惠的,或者在惠及一方的同时而无损于另一方;第二,重复性也致使一种 信赖和信用,能遏制欺诈行为。他觉得大家所说的伦理学应是指一套与别人买卖的 规则,这类规则禁止损人利己的行为,而弄清一套古往今来大家广泛同意的行为戒 律与功用最大化行为的一致性是大概的。
时光过去了二百多年,大家生活的年代毕竟和亚当·斯密的年代已经相当不同 了,今天学科的分工日益精细明确,绝大部分的学者不会像二百年前的很多学者那 样横跨好几个范围并获得骄人的成绩了。大家的主要精力也应该放在我们的学科、 我们的专业上,任一学科的学者都要了解我们的限制和范围,有所限制也才能有所 作为。
但,大家也要时常提醒自己,各学科只不过整理和讲解世界的一个图式、一种 察看角度,而现实的生活世界事实上是一体的,这世界上发生的很多问题也常常是 关系到多方面的,譬如说收入的分配,常常既是经济学的问题,又是伦理学的问题, 还非常可能是法学的问题。所以,大家常常会遇见假如仅仅局限于本学科就难于解决 的难点,大家有时“越界”,正是被本学科中的某些问题所逼出来的。各学科在 思想方法、剖析办法乃至讲解风格上也都可以互相启发。所以,大家又有一种走向 其他学科,向其他范围的学者学习的愿望。对于很多跨学科的问题,大家有时恰恰 需要一些有关范围内的学者,依据各自的常识和练习来察看和处置这同一个问题, 而并无必要改变身份。察看学术进步和学科分化的历史,人文、哲学的范围可以说 是很多近代以来新产生的社会科学学科的“母体”,所以,今天的经济学家时常涉 人伦理学范围也就不是“扩张”了,而不如说是返回“母体”。这种作为“母体” 的学术范围有着一些大家大伙一同关心和熟知的内容,或许正是因此之故,一般来 说,伦理学者对某些纯经济学的问题几乎没办法置喙,而经济学家却常常能对道德问 题发表非常不错的建议。最后大家还是回到念书,无论怎么样,对于亚当·斯密的这两本 书,我想可以合观之,这不论对伦理学学者还是经济学学者,大概都会是一件启发 心智的事情。
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
点击数:877 | 发布时间:2025-06-18 | 来源:www.okyizu.com
- THE END
声明:本站部分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如不慎侵害的您的权益,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
-
- 学习交流 -
-
欢迎加入中国考试人事网,与万千考友一起备考

- 成考路上不再孤单
专业院校
-
关注“考试直通车”
-
领取备考大礼包
-

点我咨询
返回顶部
Copyright©2018-2024 中国考试人事网(https://www.bzgdwl.com/)
All Rights Reserverd ICP备18037099号-1

-

中国考试人事网微博
-

中国考试人事网